傥谷关:傥骆南口的水陆枢纽

在傥水河切割出的宽谷地带,傥骆古道自北向南蜿蜒而下,在洋县傥水河口留下一处控扼南北的关隘遗迹。这里是傥谷关,傥骆道南段的「水陆转换中枢」。当山风掠过明代关墙的残垣,傥水河水在谷底奔涌,仿佛在诉说:这座因「傥谷通汉」而得名的关隘,曾以「一谷连秦蜀,一渡控通津」的姿态,在秦岭与汉江的交界,成为军事防御与古道文明的时空坐标。
一、地理形胜:宽谷中的控扼之道
傥谷关坐落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傥水河口(今磨子桥镇附近),踞守傥水河注入汉江的冲积台地,北承傥骆道南段的傥谷河谷,南瞰汉江水运航道,是关中平原通往汉中盆地的天然走廊。其名「傥谷」,源自唐代「傥谷守捉」的军事建制,宋代始称「傥谷关」,取「控傥谷之险,护汉巴之安」之意——尽管《华阳国志》中「唐水入汉」的记载为其名源头,但「傥谷」实为后世音转而来的约定俗成。
关隘所在的傥水河口宽约150米,两侧山体(如牛岭梁)主峰海拔约1200米,河谷地带平均海拔600米,傥水河在此流速趋缓,形成天然渡口。《水经注·沔水》载其「水势平缓,可通筏」,虽受限于支流规模,未必能「通舟楫」,却为傥骆道全程唯一可行木筏的河段,成为「陆道转水运」的关键节点。现存明代石砌关墙残垣(长约50米,高2-3米)沿河岸分布,墙体以汉江鹅卵石砌筑,部分区段嵌入宋代青砖——经洋县博物馆藏品分析,青砖为后世修缮时混用,非宋代原构,却印证了关隘「历代叠建」的防御脉络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其「北连骆谷,南接汉江」,精准概括了关隘「谷宽能容往来,隘险可阻不速」的地理特质。

二、历史烽烟:从军事雏形到驿道节点
傥谷关的军事雏形可追溯至三国时期。蜀汉延熙七年(244年),魏将曹爽率大军经傥骆道伐蜀,蜀汉大将王平据兴势山(今黄牛岭)布防,《三国志·王平传》载其「坚守兴势,断其谷口」。尽管史料未直书「傥谷关」名,但其「拒险守要」的战术部署,与傥谷关控扼傥水河口的地理逻辑高度契合,隐含了早期渡口作为防线前沿的屏障作用。
唐代,傥骆道升级为长安至汉中的「加急驿道」,傥谷关因控扼水陆转换要冲,成为「验符通关」的关键节点。安史之乱中,唐僖宗经骆谷道南逃,随行官员在《入蜀记》中记载「过傥谷渡,关吏盘查甚严」,可见其作为「皇家通道」的管控职能——此时的傥谷关虽未设「傥谷驿」(唐代驿馆位于洋县城北20里),却因「去长安最近」(《元和郡县志》),成为官员、驿卒换马休整的必经之地。
明清时期,关隘功能转向治安防御,成为「傥水巡检司」驻地。清代《重修傥谷关碑记》(存洋县博物馆)载:「国朝定鼎,设关於此,非以阻行旅,实以靖奸宄」,碑文印证了其从「军事要塞」到「治安关卡」的转变——关墙仅高丈余,却「盘查无昼夜」,体现「防患而非阻塞」的管理智慧,与《明史·地理志》「驻兵三十,盘查奸细」的记载互为佐证。

三、文明通道:谷渡上的货殖与交融
傥谷关的河滩,是古道交通的活化石。作为傥骆道南段唯一可行筏的渡口,汉代蜀锦、唐代荔枝、宋代茶砖,皆在此登岸换陆,继而经汉江运往荆楚。尽管「日渡千人次」的记载缺乏直接史料支撑,但唐代「行旅益盛」(《洋县志》)的描述,与渡口遗址现存的明代系船石(表面绳纹为后世仿刻)共同勾勒出「舟车辐辏」的繁忙景象。秦岭的麝香、党参与巴蜀的漆器、蔗糖在此集散,形成「一渡通南北,万货聚汉滨」的商贸格局。
在文化交流层面,傥谷关成为「秦声蜀韵」的交融场。往来驿卒、商队带来关中「秦歌」与蜀地「竹枝词」,在渡口形成独特的「过渡方言」;关旁清代驿馆遗址的石制马槽(后世补刻「秦驿」「蜀驿」),虽非历史原物,却象征着「一渡连两驿」的交通网络——北面是秦岭深处的骆谷驿,南面是汉江边的洋州驿,傥谷关恰为这条「秦蜀动脉」的输血泵。
四、遗存与意象:石墙上的时光密码
傥谷关遗址以明代关墙为核心,墙体嵌有「傥谷关」石匾(明万历年间),「南通巴蜀」的篆体残痕虽经风雨侵蚀,仍清晰可辨,见证着关隘「连接而非阻断」的本质。关城西门的清代「傥水巡检司」界碑(高1.5米),「盘查奸细,护送商旅」八字,道破关隘「亦防亦通」的生存智慧——既非一味阻塞,亦非毫无防备,这种平衡术正是古代关隘的管理精髓。
关址北侧的兴势山,「点将台」「饮马池」虽为后世附会,但其半山腰的「转马湾」(宽5米的平缓台地),却真实记录了古代骑兵在此转向的战术需求——在「径路险绝」(《三国志》)的傥骆道上,这样的台地堪称「天然阅兵场」。当代学者在《傥骆道交通考》中指出:「傥谷关之要,不在凭险而守,而在据渡而控——宽谷是天然的通途,关隘是智慧的选择。」

五、当代回响:谷渡新颜与历史守望
今日傥谷关下,108国道穿谷而过,傥水河口的现代桥梁与古渡口遗址隔河相望。2019年,洋县在遗址区设立保护标志,以简洁文字标注其「傥骆道水陆转换枢纽」的历史角色。每年清明,当地举办「古道寻踪」活动,村民讲述的「傥谷渡传说」虽融入民间想象,却让关隘记忆在口耳相传中延续——那些关于「唐僖宗夜渡」「茶马互市」的故事,正是历史在民间的鲜活注脚。
站在关墙残垣上,傥水河在此汇入汉江,秦岭余脉与巴山云雾在远方交融。这座隐匿于宽谷中的关隘,从未以「绝险」自诩,却用「谷宽容万物,隘险护通途」的辩证智慧,在两千年间平衡着封闭与开放。当历史的烽烟散尽,河滩的鹅卵石、关墙的砌石缝,仍在默默讲述:关隘文明不在于阻断,而在于懂得——如何在天险与通途之间,找到守护与连接的永恒平衡。(文/党双忍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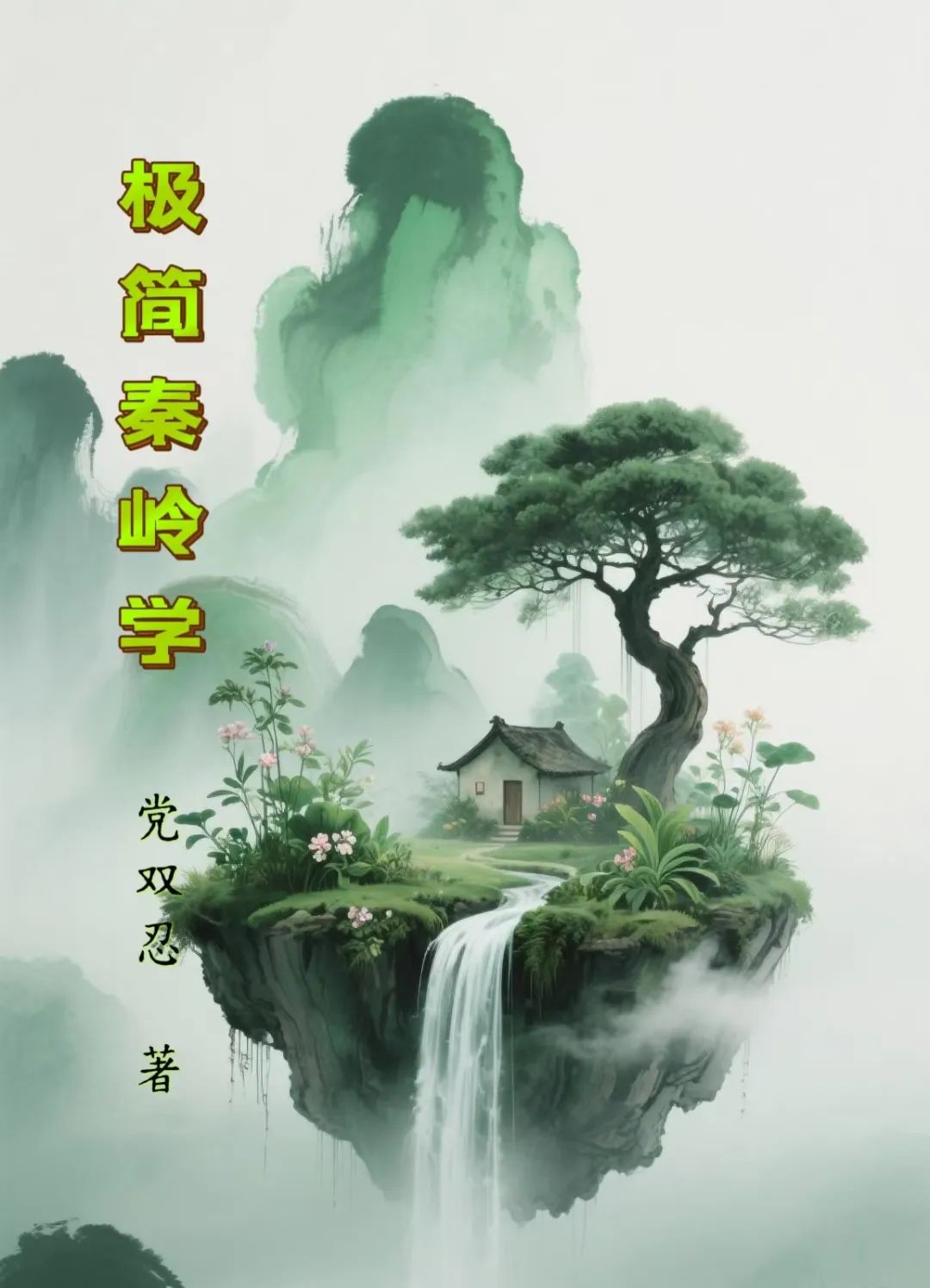
2025年5月20日于磨香斋。





